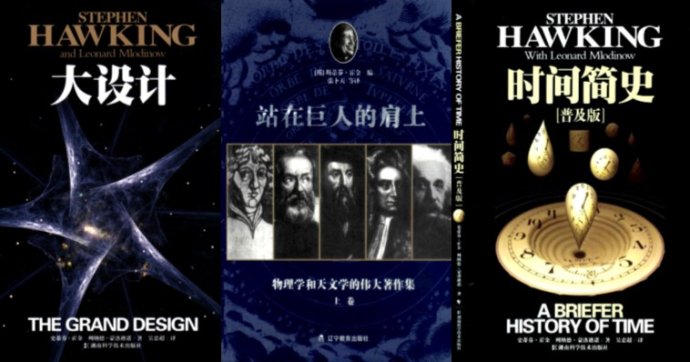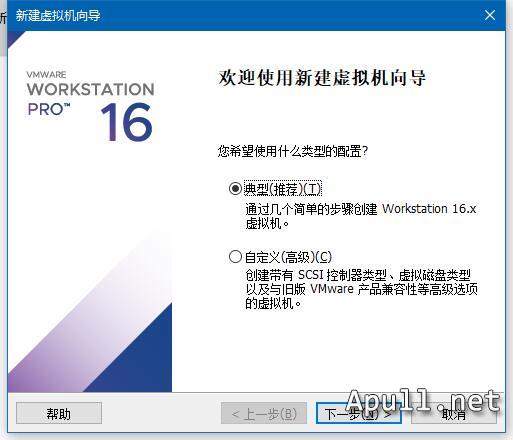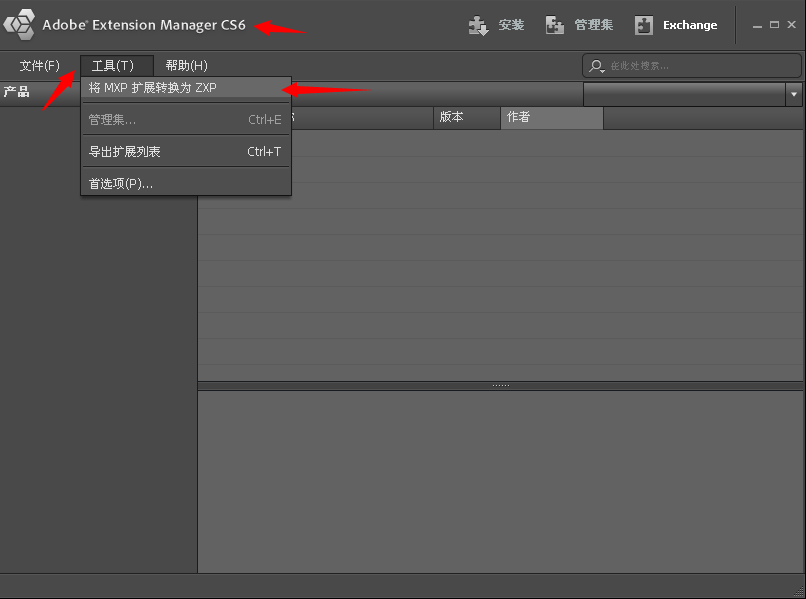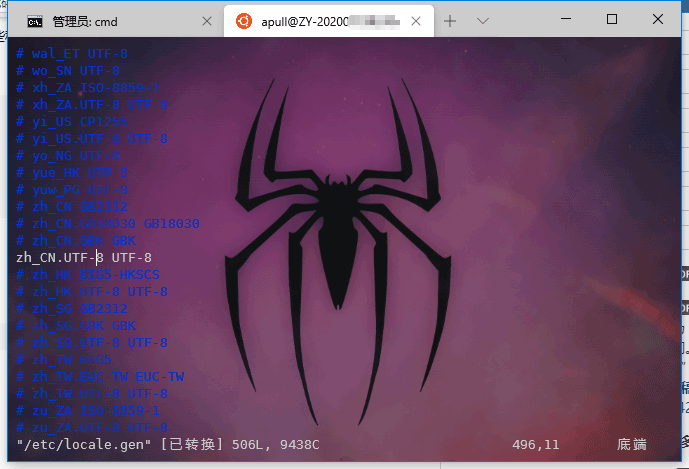霍金:一个“科学之神”的打造及其意义
霍金:一个“科学之神”的打造及其意义
□ 江晓原 ■ 刘 兵
《时间简史》,霍金著,许明贤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果壳中的宇宙》,霍金著,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大设计》,霍金著,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宇宙简史》,霍金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乔治开启宇宙的秘密钥匙》,霍金等著,杜欣欣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乔治的宇宙寻宝记》,霍金等著,杜欣欣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站在巨人的肩上》,霍金编,张卜天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 刘兵兄,要讨论霍金,你自然是“当仁不让”了——你是为霍金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十年前你为霍金《时间简史》中译本策划的广告语“阅读霍金,懂与不懂都是收获”,至今仍被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用在《大设计》中译本的营销上。《时间简史》在中国销售上百万册,这其中你的广告语起了多大作用,倒也不容易“量化考核”呢。但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广告策划。
说实话,在《时间简史》畅销中国的时候,我对霍金尚未发生太大的兴趣。当然我也未能免俗地弄了一本《时间简史》来看看,甚至还和你谈论过这本书。我真正对霍金其人其事发生兴趣,还是去年的事情。2010年,霍金对人类的三个大问题:上帝、外星人、世界的真实性,发表了明确的意见,不出所料地在媒体上引起了巨大关注,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媒体为此来采访我,和大部分人关注他的表态内容不同,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为何要在此时就这三个问题表态?由此引发了我对他的兴趣。我关注他的结果之一是,和穆蕴秋小姐联名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霍金的意义:上帝、外星人和世界的真实性》的论文。
霍金真正的“学术著作”,其实迄今为止并未引进中国——我想那是因为它们实在太抽象太枯燥乏味了,一般公众无法“消受”它们。上面开列了七种霍金著作的中译本,其中第五、第六种是霍金和他的女儿合著的科幻小说,第七种是霍金编选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五位科学伟人的著作,霍金为这五位伟人写了他们的“生平与著作”。前面四种则是霍金自己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是《时间简史》和《大设计》。
■ 我突然想到,我们在这个栏目中谈了这么久,居然到现在才谈霍金!而且,从我们的专业,从我们以前对科普及相关类图书的关注,以及我们曾在《文汇读书周报》的南腔北调专栏中谈霍金的书这些背景来看,这个拖了很久的选择,也许反映了我们在深层的心理中对霍金的某种评价,或是潜意识中的某种有意忽视?
你提到的我想出的关于霍金著作的广告语,其实在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会有如此反响,在媒体上如此多按此句式的模仿(这也算是影响的一种表现吧),甚至于一些争论(比如在《科学时报》上)。当时,很有些更关注如何把霍金的书推销出去,觉得让人们至少看过他的书,才算是某种有效的科普传播。只是现在事后想起来,觉得这话暗中似乎有点道理,也有点不讲道理。
说到霍金,其实,我还曾有幸当面听过一次他的讲座,那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在读研究生,而霍金的《时间简史》也还尚未出版,至少在公众中他的名声还不像后来那么如雷贯耳。那是在霍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做的有关宇宙学方面的讲座,我还记得,在他带的公文箱中,还放着一本爱因斯坦的传记《上帝是不可捉摸的》。
后来,霍金成为科普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科学家,是与他的《时间简史》这本著作的出版密切相关的。这本书曾在国内出版了不止一个译本,但直到湖南科技出版社收在“第一推动丛书”中的译本出版后,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记得,当时许多人买这本书放在书架上,甚至成为某种时尚。其实,这本“科普”著作并不能算是通俗,没有科学背景的人,甚至于物理学背景稍差的人,要想读“懂”它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也是我想出那句广告语的另一个背景。至于为什么这本书会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火”起来,应该算是值得科普界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只是直到现在,我似乎还没看到过真正让我信服的解释。也许,他的身体状况与其智力的反差也会是一个重要因素?
□ 在我对霍金的著作本身发生兴趣之前,我对于“霍金为什么会红”这个问题的兴趣要大得多。我认为霍金是“科学传播学”——如果真有这种学问的话——上一个极其特殊的个案。
从湖南科技出版社次第出版的“第一推动丛书”中的许多书就可以看出,其实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这样的书,在当代有关物理学的读物中,并无多少特立独行横空出世之处。但怪就怪在,别人的书,也就是普通的书而已,只有霍金的《时间简史》,畅销全球,相传全世界每7人个人就有一册《时间简史》;此书中译本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量,据出版社介绍,算上“插图版”、“普及版”,也超过了百万册。霍金确实成为成为一个科学传播的神话。
这个神话之所以能够形成,表面上的原因似乎也不难找出几条:一、你所说的“他的身体状况与其智力的反差”;二、电视等媒体对他的大力推介和包装;三、他的书内容比较有趣。但是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后面两条理由其实是相当无力的——事实上,《时间简史》的内容很难谈得上“有趣”,对绝大部分公众来说也是很难真正理解的。成为媒体的宠儿固然有助于他的书畅销,但这只是将问题转换了而已——霍金为何能成为媒体的宠儿,依然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成为媒体的宠儿有助于他的书畅销”的推理能够成立,那么,将问题转换也许并非没有意义——当我们将问题“《时间简史》为何畅销”转换为另一个问题“霍金为何能够成为媒体的宠儿”后,我们的认识是不是有可能往前走一步呢?
■ 关于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即“霍金为何能够成为媒体的宠儿”,恐怕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大胆的猜想了。其实,对这样的问题的回答,本来就不唯一,而且,在各种回答中哪个“正确”,恐怕也没有标准的判据,只能根据个人的偏好,以及哪个答案听上去似乎更有说服力来选择了。
这样,要我来猜,我想应该是若干因素结合的结果。
其一,科学普及读物本是图书出版中的一大类,应该有可能“建构”出畅销书。
其二,霍金本人的身体状况,他患有严重疾病,甚至后来连说话都不能自己而要靠机器,这与他居然还能从事被常人认为极难理解的科学研究,形成了对比极强的反差,因而也就让人对其有所好奇,造成一种悬念。(这里也许可以补充一个情节,当年我听霍金讲座时,他还没用机器来说话,而是先对助手讲一通别人都听不清楚也听不懂的话,然后,由助手翻译成英语,最后再由译者译成中文。)
其三,霍金的书里所讲的内容,恰恰又是在诸多科学学科中最难懂的物理学,而且主要是宇宙学,但像宇宙学这样的主题,是多年来人们在各门科学中相对较有兴趣的,因而康德才会将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当作人们最为突出关心的主题。
其四,在前三个要素存在的前提下,媒体将他包装成一个科学明星。最后导致在公众中形成一种时尚,如果不知道霍金,如果书架上没有一本霍金的书(也许读没读过,读没读懂都不是最重要的),就会成为很out,很没有文化,很没有品味的人。霍金的书成了一种时尚的标签。这与其他一些略带皇帝新衣特点的时尚追风,其实是很有些相似之处的。这也再次印证了,一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经常地并不是由于其内容,因而当人们“策划”畅销书时,最主要花力气的,也经常不是放在写作上。
就我本人的经历,我就见过许多朋友和认识的人坦言读不懂霍金的书,这其中甚至于包括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就更不用说所受的教育训练是文科背景的人了。但他们却大多知道霍金和他的书!
□ 你的猜想我大体是同意的,但也有一点补充。你上面所说的第四点,实际上主要是效果而非原因。而对于霍金能够成为媒体的宠儿,许多人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大家见到某某人成了媒体的宠儿,许多人是这样猜测其原因的:他(她)和媒体有关系;或是他(她)运气好碰巧被媒体看中;或是他(她)买通、贿赂了媒体等等。其实,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些猜测都是不能成立的。
这些年我们两人都常和媒体打一点交道,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体会,霍金成为媒体宠儿的实际情形估计是这样的:媒体其实经常在寻找自己的“明星资源”,霍金最初进入媒体的视野,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仅仅进入媒体的视野,还远远不能使他成为媒体的宠儿。霍金这样的学术明星,被媒体选择作为自己的宠儿,需要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他有足够的学术地位和声望;
二、他愿意和媒体打交道;
三、他的研究和活动能够为媒体提供话题;
四、他有足够强的公众话语能力。
从霍金的情况来看,上面这四个条件他都非常符合。所以,尽管进入媒体视野的学者肯定远远不止霍金一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考察(比如接受访谈、做做谈话节目之类)和筛选,霍金明显胜出,被选定为大力包装推出的明星。“宠儿”地位至此遂告确立。
再进而言之,在上述四个条件中,符合第一个条件的学者当然不少,但后面三条还要同时符合就很难了。
第二条取决于该学者的天性。
第三条取决于他对自己学术领域的选择——而当一个学者早年选定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几乎没有人会以“将来能够为媒体提供话题”作为考量之一,所以等到自己功成名就之后,即使变得很想和媒体打交道,但早年选定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参数。
第四条也和天性有关,但同时还直接关系到该学者的能力。如果该学者思想保守,头脑冬烘,语言乏味,那他即使非常想在媒体上出风头,媒体也不会选择他。
■ 你的补充,我觉得也都言之成理。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一旦霍金的书成了超级畅销书,而多数人又读不懂时,会有什么后果。
2006年时,有署名辛普里的文章发表在《科学时报》上,批评我那句“阅读霍金,懂与不懂都是收获”的广告语,认为那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忽悠”,文章说:“这种煽动崇拜和赞美的科学传播究竟对于促进理解科学有多大帮助,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实际上,有许多证据说明,许多科普书籍和刊物的最热心读者恰恰是那些许多以科学普及为己任者所痛心疾首的对象——民科。他们的问题正是对科学有热情,而对实际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掌握太少。因此,‘不懂也是收获’的广告实际上正是鼓励了这些民科们的研究活动。”辛文还说,“在这种不懂也有收获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科学主义者的‘缺失模型’,只不过这里传播行为想要提供的不是尽量减少公众与科学家之间的知识距离,而是保证公众永远崇拜和臣服于科学家的关系被复制和强化。科学文化人说他们的缺省配置是科学主义,从他们苦心发明的这句广告用语中可以看出这至少对他们来说是真实不虚的。科学主义的尾巴可不是一天就能割完的呀!”
后来,我也曾撰文“你才科学主义呢!——简答辛普里的‘不懂也是收获’” 在《科学时报》上发表。其中的要点,一是强调科学的娱乐功能,二是认为公众的“懂”与科学家的“懂”是不一样的(关于这点在后来我又有专门的文章论及),三是认为这种批评有对“民科”的歧视之嫌,四是强调这仅仅是句广告语而已。对于其中的第三点,后来,我带的一个研究生的研究给出了相关的证据,即中高端科普读物的重要读者群之一,就是“民科”。而关于“民科”问题,在我们两人共同主编的《我们的科学文化》中《阳光下的民科》那一册中,我再次提出了“民科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看法。
□ 我那时也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文章支持你的辩解,但我觉得你的辩解还不够有力。在我看来,读某种东西,不懂但是有收获,原是常见之事。当年梁启超论李商隐无题诗,就有读不懂但觉其美的著名说法,觉其美不就是一种收获吗?不就是潜移默化、精神熏陶吗?如果说梁启超李商隐都太高远了,那我还可以举出更贴近的例子:我熟识的人文学者朋友中,不止一个向我表示过这样的想法:对于科学大师的原作,我知道自己看不懂,但就是想看一看,那些著作到底是怎样写的,是什么模样。如果有人以这样的心态,去阅读了霍金的《时间简史》,或者更难懂的经典,比如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他有没有收获?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再进一步说,霍金所研究的那些领域,其实已经到了传统科学领地的边缘,在这样的边缘地带,“懂”与“不懂”也开始难以明确界定了。有些问题追究到深处,已经变成是不是接受某种约定、用不用某种语言的问题,它们有可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知识传播中“懂”与“不懂”的境界。对于霍金所研究的一些问题,除了霍金等一小群物理学家之外,就广大公众而言,“懂”与“不懂”有可能已经失去传统语境中的意义。我认为这也许恰恰是你当年那句广告语的深刻之处。
当然,在你的那句广告语中,确实暗含了“霍金是大师”、“霍金的著作是经典”这样的前提判断。但我们确实也不必对霍金的所有作品都五体投地。例如,霍金和他的女儿合著的两种科幻小说,《乔治开启宇宙的秘密钥匙》和《乔治的宇宙寻宝记》,基本上就是停留在科幻最低境界——科普——中的作品。虽然书中也有“科学可以做大量的好事,也可以造成巨大的灾难”这样的大师应有之语,但总的来说实属乏善可陈。以至于我在听别人简介书中情节并描述阅读感受之后,问出的第一句话竟是:“这真是霍金写的吗?”
■ 说起来,个人的看法,也应该是“与时俱进”才对,这不是指赶时尚,而是因为思考和研究而有变化。几年之后,反思起来,我与当时写反驳文章时相比,应该说立场还是有些变化的。现在我会承认,当时确实还是有些“科学主义”尾巴没有割干净。尽管你说也不一定非要割干净,但在我个人的倾向中,还是觉得割得更干净些为好。这主要是指,那句广告语,确实还是隐含了一些要阅读霍金这样主流科学大师的作品,会对传播主流科学知识有积极的作用,哪怕只是有限的,不那么真被看懂的传播。
时至今日,再要我来分析评论,首先,我会以有限的方式来为那句广告语再做些辩护,即科普作品,以及一切其他作品,尤其是不那么好懂的作品,在阅读中,读者的背景不同,阅读目标不同,很可能就会读出不同的东西。例如,为“民科”所爱的科普阅读,在更大程度上可能就无法达到原来作者设定的目标,但这种在阅读中的创造,也是一种好事,何必只有一种理解呢?其次,也许在倡导人们阅读霍金以及其他主流科学大家的科普作品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其他一些亦可归入广义的科普的、非主流的作品,包括涉及地方性知识的科普作品,这样,才有利于在一种平衡中,保持科学的多元文化的传播。这后一点,其实是目前更为缺乏的。
说了这么多有关阅读霍金的意义之后,也许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谈一些他的书中涉及的观点,特别是涉及到对世界的认识、科学的本质之类的带有哲学意味的观点了。这尤其体现在最新的《大设计》中。你曾专门写过文章,包括学术文本,来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尝试在里讲讲呢?
□ 我觉得《大设计》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是书中的第三章“何为真实”(What Is Reality?)。
霍金假定有一个鱼缸,里面的金鱼透过弧形的鱼缸玻璃观察外面的世界,如果金鱼中也有物理学家,而且它们也归纳观察到的现象,并建立起一些物理学定律,这些物理定律也能够解释和描述金鱼们透过鱼缸所观察到的外部世界,甚至还能够正确预言外部世界的新现象的话,这样的“金鱼物理学”可以是正确的吗?
霍金断定,这些金鱼的物理学定律,将和我们人类现今的物理学定律有很大不同,比如,我们看到的直线运动可能在“金鱼物理学”中表现为曲线运动。但他接着问道:“我们何以得知我们拥有真正的没被歪曲的实在图像?……金鱼的实在图像与我们的不同,然而我们能肯定它比我们的更不真实吗?”
按照我们以前所习惯的想法——这种想法是我们从小受教育的时候就被持续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这样的“金鱼物理学”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金鱼物理学”与我们今天的物理学定律相冲突,而我们今天的物理学定律被认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将今天对(我们所观察到的)外部世界的描述定义为“真实”或“客观事实”,而将所有与我们今天不一致的描述——不管来自金鱼物理学家还是来自前代人类物理学家——都判定为不正确。所以霍金明确指出:“那不是真的。……人们可以利用任一种图像作为宇宙的模型。”霍金接下去举的例子是科幻影片影片《黑客帝国》(Matrix,1999~2003)——在《黑客帝国》中,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受到了颠覆性的质疑。
霍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性概念(There is no picture- or theory-independent concept of reality)”。他所认同的是一种“依赖模型的实在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对此他有非常明确的概述:“一个物理理论和世界图像是一个模型(通常具有数学性质),以及一组将这个模型的元素和观测连接的规则。”霍金特别强调了他所提出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在科学上的基础理论意义,视之为“一个用以解释现代科学的框架”。
霍金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马上会让人联想到哲学史上的贝克莱主教(George Berkeley,1685~1753)和他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非常明显,霍金所说的理论、图像或模型,其实就是贝克莱用以“感知”的工具或途径。这种关联可以从霍金“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性概念”的论断得到有力支持。
在哲学上,一直存在着“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前者相信存在着一个客观外部世界,这个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人类观察、研究、理解它与否,它都同样存在着。后者则否认这样一个“纯粹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比如“只能在感知的意义上”承认有一个外部世界。现在霍金以“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性概念”的哲学宣言,正式加入了“反实在论”阵营。
■ 以前,人们经常会注意到一件事,即那些顶级的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到最后,关心讨论的都是非常哲学的问题。在霍金这里,似乎也是一样。
但是,物理学,究其根源,确实是与哲学分不开的。只不过,现实中,更多的更为注意实际应用或技术性技巧的物理学家,经常不那么关心哲学,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分工,而且这种分工也就经常地把他们分在了顶级物理学家的阵营之外。
你前面在讲人们习惯的观念时,用了“被持续灌输”这一说法。确实如此!我们的教育,似乎一直就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我们如何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这个“客观世界”及其“客观规律”是如何“不以人的意动为转移”的。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教育却没有告诉受教育者,这本是一个超验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更没有告诉受教育者,在哲学领域中,与这样的本体论对立的观点,也可能是有价值的。在这样的默认前提下,当人们再接受科学教育时,就被强行地把科学家们所认识到的“规律”等同于唯一的、客观的、与人的认识无关的规律或真理。而在科学家们当中,则或是因为不关心哲学,而不加思考地就承认了(或者根本就是无视)这样的命题,或是因为基于物理学的研究真正进行了哲学思考,而对这样的命题有所置疑。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毕竟分工还是存在,毕竟科学家的主要工作不是进行哲学研究,当科学家们结合自己的科学研究,结合自己对科学研究的体会和反思,来真正进行一些相关的哲学思考时,他们往往并不一定就是提出了最为独特、原创的哲学理论,而只是以接近于已有的哲学理论的方式在选择立场和讨论问题(连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和霍金也是如此)——尽管有时也偶有例外。
在以科学、科学家、科学研究方式为研究对像的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研究领域中,科学理论的社会建构观点,早就与传统哲学相似地,把已经出现的哲学观点体现和推广到科学的问题上了。在这样的意义上,霍金的哲学讨论,在哲学上也许算不上如何了不起,但恰恰因为社会上在传统中存在的对科学的特殊敬意,恰恰因为像霍金这样的顶级科学家同时又是科学明星,所以,霍金在《大设计》中这些观点的表述,仍然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也成为霍金作为一个顶级科学家的一种象征——他毕竟在实是求事地进行着对于一些终极问题的哲学思考。